三年前,我们曾记录下一个男人内心最深处的渴望。夏程作为一个左腿残疾、曾因高烧导致斜视的男人——将他最大的梦想,坦诚地摊开在所有人面前:他只想拥有一份在普通人看来或许寻常,于他却遥不可及的爱情。
时间给出了回响。 如今,那个寓言即将迎来它最温暖的结局:他要结婚了。
这条路,他走得很慢,一瘸一拐,走了三十多年。他身上所承载的,是一个男人最为原始的坚持:当世界试图定义你为“残缺”,你偏要证明自己灵魂的完整;当现实一次次暗示你“不配”,你内心关于爱的火种却从未熄灭。
祝他新婚快乐,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
婚礼前夜
夏程(冷平)的手,现在握笔还是有些颤抖。
他正在一张婚礼请柬上,写下又一个名字。周围很安静,笔尖划过纸面,发出沙沙的轻响。这让他偶尔会走神——想起很多年前,在骗人的成功学课堂上,他蜷在角落,名字写得歪斜局促,像怕被看见。
那时他花一万块钱,买一个被平等注视的座位。
他告诉我说,心疼钱是真的,但不后悔,因为那里就像个乌托邦,里面的讲师们个个都重视他,不会因为他是个残疾人而露出鄙夷或轻视。即便花一万块钱买被别人尊重,他也觉得很值。在成功学课堂待了三个月,临走时他问讲师:“如何才能成功?”
讲师告诉他:“只要你干成一件你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干成的事,那你就成功了!”什么是自认为不可能干成的事?夏程想了好久,最后得出一个答案:谈一场简单的恋爱!
从南下的火车到流水线的轰鸣,从招聘者的白眼到出租屋的孤寂,那是一种漫长得没有尽头的“性压抑”与“爱压抑”。
直到在网上找到饺子和浪迹,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。
随后参加“蓉城”线下课,在春熙路练习搭讪,从开场就吓跑女生,到调整话术,终于能平等地和陌生人聊上五分钟。
他记得在Space夜场,被带上DJ台前最炸裂的位置,在濒临崩溃的边缘,把二十多年的委屈、痛苦、煎熬随着呐喊全部倾泻,泪流满面。
那次之后,他微信里开始有了十几、二十个新认识的女孩。
这么多年过去,夏程始终记得那一对萝莉闺蜜。遇到她们之前,他已经在街头徘徊了一个多小时,前面几个女生知道他来意后,都会不自觉得撇一下嘴,翻了个白眼,敷衍的的说“不了不了”,头也不回的加速离开。
那对闺蜜没有嫌弃他,停下来聊了整整五分钟,还给了他微信号。“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,成功的在大街上认识了一个陌生女孩,并且彼此平等、尊重的交流了几分钟,我好像是个正常人了。”
也就是从那一刻起,夏程“站”了起来,后面有位女生还发了一个朋友圈,他截图保存至今。
可怜瘸子
夏程会一直记得那一天,1995年8月的那个傍晚。具体的日期已经模糊在岁月里,但那种感觉穿透了三十年,依然锋利——先是腾空,然后是“咚”的一声闷响,像命运落下的印章,重重盖在一个五岁男孩的后半生。
他从约五米高的地方摔在一块硬石头上,世界瞬间被剧烈的疼痛刷成空白。一种本能的恐惧攥住了他,他没敢立刻告诉家里。疼痛可以忍受,但成为家人的负担,让年幼的他更害怕。
几天后,左腿肿得发亮,疼得完全沾不了地,在父亲严厉的逼问下,他才吐露实情。用今天的话说,那或许只是一次复杂的骨折。
但贫穷,让“或许”变成了冰冷的“必然”。
父亲没有能力带他去城里的医院,只能背着他,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,寻找传闻中会接骨的“先生”。错位的骨骼在一次次粗糙的复位中,不可逆转地长成了残疾的模样。
然而,命运的试炼才刚开始。一年后,他摔伤了左手,同样的土方接骨,留下了终生无法控制的微颤和明显的发育萎缩。几个月后,一场持续数日的高烧,像一场无声的火灾,将他的右眼烧成了无法对焦的斜视。
他曾自嘲:“屌丝还分三六九等,像我这种,简直是不入流。”不入流的人生,意味着从起点就被推出了主流轨道。
校园并非庇护所,而是残酷的预演。小学,同学们模仿他走路一瘸一拐的姿势。初中,他成了坏学生随手可取的出气筒。他开始逃学,把自己藏在无人处,成绩一落千丈。
唯一的暖色,是职高时一位对他格外热情的同桌女生,让他误以为看见了爱情的微光。当他鼓起全部勇气表白,得到的回应是:“你误会了,我对你好,只是觉得你很可怜。”
“可怜” 这个词比“瘸子”更锋利,它否定的不是身体,而是作为一个男性、一个人的全部吸引力和价值。
毕业晚会,班主任问每个人的梦想。轮到他时,这个躲在角落的年轻人,在哄笑和戏谑的目光中站起来,沉默了几秒,然后对着话筒大声说:“我的梦想是谈一场简单的恋爱!”
全班爆发出更大的笑声,连老师也笑了。他嘴角扯了扯,也跟着笑了。那笑容,是他青春期最后的盔甲。
简单爱情
现在的妻子,让他从内心笃定:他们的感情是爱,而不是可怜。
遇到她之前,夏程很认真地追求一个女孩,那个女孩长得并不漂亮,个子也不高,右腿跟他一样,也是残疾。他以为两个瘸子在一起,总该能结婚。但表白的时候,仍被拒绝了,女孩拒绝他的理由非常现实:
“对不起,我虽然残疾,可我只想找个四肢健全的男人!”
此时他开始总结自己过去的不足:形象、认知,以及身体上可调整的部分。他花大价钱做了斜视矫正手术,穿搭、健身、拍照,构建新的展示面。
他清晰地认识到,吸引力不只是“对女人好”,更是综合价值的呈现。当妻子被问及看中他什么时,答案是“脾气好,性格好,能包容”,是他思想上的成熟和对事物的态度。
他和妻子,相识于太古里。那是2023年7月,初次见面并无波澜,像都市里大多数谨慎的试探,聊了天,看了电影,之后便沉寂下去,沦为朋友圈点赞之交。
直到2024年国庆,他发了一条动态:“国庆有没有孤儿在成都”。她点了赞,私聊的窗口就此重新打开。
从线上寒暄,到来福士一起买菜、做饭、看电影,节奏平缓得像秋天的溪流。
真正的转折在于一种无形的“默契”。他说,很多时候话还没出口,对方已经想到。早晨醒来,两人会同时问对方“要不要吃饭”;做饭时自然分工,一个掌勺,另一个就打下手洗碗。
这种日常琐碎中滋生的共鸣,比任何戏剧性的开场都更坚实。2024年10月30日,他正式表白。11月1日,他们在一起。一切快得不可思议,却又水到渠成。
关系的下一个刻度,是见父母。他知道那将是一场无声的评估。果不其然,女孩母亲的心疼与失落,还是辗转传到了他耳中。
“女儿找了一圈,找了个残废。”这话尖锐,却真实。
然而,后续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。对方家庭展现出一种务实的温情。双方父母见面,氛围平和。他们提出的要求具体而简单:不需要彩礼,不要求买房(女方在成都有房),只希望他能为未来的孩子存下一笔三十万的“养娃钱”。
“我觉得挺好的。”夏程语气里有一种被平等对待的坦然,“不要求我买房,就是一个很大的让步。”这条件与其说是门槛,不如说是一种将他纳入未来规划的接纳。他从中感受到的不是施舍,而是责任共担的认可。
如今,周末的生活是回丈母娘家,或出去露营。或是两人在家远程工作,一起做饭。他少年时在毕业晚会上喊出的梦想——“谈一场简单的恋爱”,如今早已达成。
新的梦想具体而朴实:“搞钱,养孩子。”孩子明年五月出生,他不打算预知性别,儿女都一样。
我问他,若孩子将来问“爸爸你的腿怎么了”,会如何回答。他没有任何犹豫:“实话实说,这东西你隐瞒是隐瞒不到的,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。”
你的名字
采访尾声,问及若有话对当年在春熙路无数次被拒绝的自己说,会是什么。夏程想了想,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。
但他说了一组数据,他手机里有上千个女生,谈过恋爱的有几十个。90%的女生还是接受不了他身体上的缺陷,剩下能接受的女生,对方父母也接受不了。
能遇到现在的妻子,其实不容易。
那个曾因“斗鸡眼”、跛足和破旧衣衫而不敢直视他人的“酷酷de男孩”(原来的微信名),此刻正平静地整理着喜帖,等待成为一名父亲,他目前还没给孩子想好名字。
父亲为他取名“冷平”,或许不曾想到,这个名字会像一个精准的预言。一个“冷”字,道尽了他童年遭遇的意外、成长中感受到的寒意与世界投来的疏离目光。而那个“平”字,则成了他一生的功课与修行。
这名字里,没有大富大贵或惊天动地,只有一个最朴素也最艰难的祝愿:愿我儿,能在人世的冷暖和坎坷中,找到自己那份寻常的平安。
为什么大家又会叫他夏程呢?
准确说,这是一个笔名。那一次改变他人生轨迹线下情感学习,对接他的公司销售叫:夏风,接待他的管家叫:苏程。他取一头一尾,当做自己的笔名“夏程”。
他感恩每一个遇到的人,也希望自己能传递这份力量。每当遇到想放弃的兄弟,他都会自信地说:“我一个残疾人都可以,你没理由不行。”
妻子也知道,如今夏程在情感行业工作。有趣的是,一次跟学员的语音沟通中,他大声的说:“把握机会,要死死干住。”当时作为女朋友的她,直接把夏程赶了出去,她心里一度怀疑,自己是不是被“搞定了”。
这是两人唯一一次矛盾,好在真诚解决了一切。夏程直接带她到公司,看自己在做些什么。坦言因为接触了这一行,才改变了自己,才有机会遇到她。离开前,妻子翻到了浪迹刚出的书《恋爱攻略》,笑呵呵地说:“呆子,你应该多学学这个。”
请柬上的名字终于写完。夏程放下笔,窗外是成都静谧的夜。
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,这是一场关于尊严的、漫长的平反。而所有平反,都需要一个像婚礼这样光芒璀璨的句点,来照亮从前所有的黑暗。
婚礼真正的仪式,已在丽江完成——一场只有他们两个人的目的地婚礼。没有亲友围观,没有繁琐流程,只有摄影师、化妆师,和雪山白云见证。
在稀薄的空气中,我们听到了:“新郎,你愿意接受这个美丽的新娘作为你的妻子,从此相互扶持、相互照顾,不论你们的一生是富是贫,是健康是疾病,都彼此相爱、相守,直到永远吗?”
“是的,我愿意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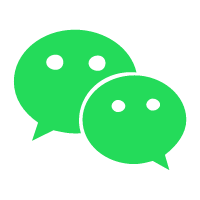




 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0921号
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0921号